| 追记总装某基地测量船大队原工程师黄亮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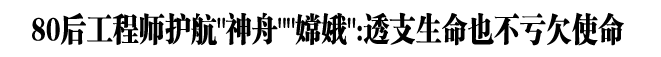
“把骨灰撒进长江”
2014年4月,癌症复发的黄亮被病魔逼到了生命的尽头,他向家人提出自己的愿望:“把我的骨灰撒进长江吧!我想永远陪伴着我的工作、我的战友。”
苗家人祖祖辈辈延续的是“土葬”习俗。最终,善良淳朴的老人情感上实在不能接受黄亮尸骨无存的现实,没有满足他骨灰撒入长江的心愿,而是选择了火葬,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驻地花山公墓。
“交最后一次党费”
在弥留之际,黄亮反复叮嘱家人要“交最后一次党费”。从昏迷中醒过来的他,醒来后最后一次唱起了他一生最爱的歌:“唱支山歌给党听,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
随后,他又一次问父亲:“我的党费交上了吗?”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
当基地领导将500元特殊党费收据交到黄亮父亲手中时,痛失爱人的黄亮妻子吴林玲早已泣不成声。
“把所有有用器官捐献给社会”
“我的器官既可以帮助别人,又可以让生命得以延续”。5月3日,黄亮脑死亡的当天上午。他反复念叨着“要把所有有用器官捐献给社会”。经过痛苦而艰难地抉择,5月7日,本不同意此举的家人决定完成黄亮的心愿,含泪在器官捐赠协议上写下“无偿捐献肾、肝、肺和眼角膜”。
然而,当驻地红十字会提出给予5万元经济补偿时,被他的家人婉言谢绝,“黄亮如果还在,他也会拒绝的”。
2006年6月,黄亮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总装某基地测量船大队。
他一到部队就赶上了新船建造,作为该船第一代船员,他幸福地说:“我赶上好时候了,做第一任船员,打三十年的基础。我现在做的是影响今后30年的工作,太有价值了,我要与船共战30年!”
平时的工作,他留给同事们的印象就是各种“超出预期”。
每天的集合训练,黄亮都是第一个到;新船安装时,在粉尘弥漫的恶劣环境里,黄亮每天爬上爬下,数千根电缆一根一根地测试,排查问题;某设备存盘数据不便于分析,黄亮独自加班钻研,编制出实用软件……
2009年2月,凭借出众的能力素质,黄亮从众多技术骨干中脱颖而出,被选拔进机关任作试参谋。
这是测量船的“0号”调度岗位,责任重大。为尽快熟悉工作,他更是每天坚持加班学习,刻苦钻研,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。
曾有一次,测量船临危受命,执行某卫星应急测控任务,黄亮仅用不到半个小时,就熟练组织部署了航线设计、方案拟制、系统协调和实战程序进入等一系列关键动作,为成功抢救卫星赢得了主动。
还有一次,测量船执行某任务时,目标海域气象恶劣,不满足海上测控条件,黄亮连夜组织论证并制定相关方案,最终,测量船向发射场区指挥部提出提前一天发射的建议并被采纳。
担任“0号”指挥员的这两年,黄亮参与组织实施“神舟”、“嫦娥”等多次测控任务,并因其工作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。
然而,常年超负荷、高强度的工作生活,黄亮早在2009年就隐隐察觉腰部疼痛,但由于身边的同事普遍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“职业病”,一心沉浸在工作中的他丝毫没有把病情放在心上。
宁可透支生命也不愿意亏欠使命——
2011年4月,黄亮借调到基地政治部负责老干部工作。带病工作的黄亮再一次干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:基地连续两年超额完成总装下达的老干部移交安置任务,所属某干休所被表彰为总装先进干休所。
“干一行,爱一行;钻一行,精一行。”同为参谋的刘高峰告诉记者,“这就是黄亮对于工作的态度。他总会把这句话打印在纸上,贴在办公桌的旁边。”
据同事们回忆,在政治部的两年中,黄亮一直是戴着腰托工作,疼得轻的时候忍着,疼得重了就起来活动几下,实在忍不住就吃几片止痛药。
“谁也劝不住他。”同事吕垚说,多少次劝他回家休息,他总说:“不要紧,手头的事没做完,休息也不安心。”
就这样,为了一句“安心”,在腰部疼痛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,黄亮始终坚守岗位,没有耽搁过一项工作。直到2013年3月,他被确诊为恶性肿瘤住院治疗。
可就是意志如此坚强的黄亮,却有着一颗分外柔软的心。
同事李仁龙还记得,有一次去驻地儿童福利院慰问,看到黄亮抱起一个智障儿童,开心地玩耍,“整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,可是没想到等他一转身,却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。”
其实,早在黄亮刚刚参加工作第一年,他就倡议大家少抽一包烟、少喝一瓶酒、少吃一包零食、捐出一份零花钱,还带头收集变卖船上的旧报纸、饮料瓶等废旧物品。“如今,这份基金仍在高效运转,连续8年资助驻地儿童福利院,已经资助2名高中生完成学业。”
平日生活节俭的黄亮,“在别人需要帮助时,他总是尽全力而为。”甚至在病重入院治疗期间,有不知情的战友找黄亮帮忙,黄亮总是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,之后再求助同事帮忙办妥。
“黄亮最大特点就是重感情。”在爱人吴林玲的眼里,黄亮之所以对工作那么“狂热”,很大程度上是不想辜负了别人的期望。黄亮住院期间常说,“我给组织做的贡献很少,却添了这么多麻烦,心里过意不去,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。”为了不再给组织增添更多的麻烦,基地派救护车接他去医院,他拒绝登车;老家亲属来探望,基地安排了住处,黄亮硬让父母退了房,八九口人挤在54平米的公寓房里……
“如果没有对军营的深情、对事业的热情、对理想的衷情,黄亮的从军道路不会走得如此坚定而精彩。”纪检处干事罗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
黄亮的初中老师杨向娥记得,黄亮初一时的那句“老师,长大后,我一定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!”
交大国防生选培办主任耿梅娟记得,大二时黄亮面对“你的专业出国机会多、毕业薪酬高,而部队待遇低、环境苦,你要考虑清楚”的规劝时的那句“我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踏踏实实为部队做点事。”
“他穿军装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很特别的自信。”妻子吴林玲记得,一次他穿着军装对着镜子边“自恋”边半开玩笑地说,“小姑娘,你没嫁错人,看你老公是多精神的一个小伙子!”说道这里,吴林玲哽咽道,“他平常总是跟我说,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”
“我不能选择生命的长度,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厚度。” 他对赶来看他的战友说,“大家不用为我难过。人这辈子就像坐公交车,我只是提前到站,但我也欣赏了沿途的风景,和大家一起奋斗过、快乐过,我很知足……”
黄亮走了,在长江之畔静静地躺着,守望着他挚爱一生的事业;而他留下的人间大爱,一如他的名字,照亮着每个人的心灵。
“不可思议”的乐观和坚强——
“病重以来,黄亮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掉过一滴眼泪。”黄亮的妈妈在一次采访中说。探病的亲友说,他那种由内而外展示出来的乐观让人觉得“不可思议”。
“他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,笑着问我那调皮的女儿最近怎样,就跟平常的寒暄一样。”
“提到他的病情,他乐呵呵地说一切向好。没事还能讲几个笑话。”
“临走时我本来想对他说加油的,可没想到他竟然反过来握着我的手,对我们说了句‘加油’。”
“病重时每有人来探望,他总要求穿戴整齐坐在轮椅上,说‘躺着不礼貌’。”
“直到他走,整个病重期间都没有留给我们什么痛苦的回忆。”
……
“他在生命的最后依然是一个强者。”这就是他留给亲友们最后的印象。